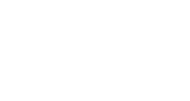张某、安徽某某种业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案号:
(2025)最高法知民终94号
案由:
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
公开类型:
公开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程序:
民事二审
发布日期:
2025-09-19
案件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5)最高法知民终9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仁,江苏民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安徽华某种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建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河南劳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琳,河南劳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因与被上诉人安徽华某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于2024年12月13日作出的(2024)苏03民初265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5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5年3月19日进行了询问。上诉人张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君仁、被上诉人华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鑫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24年6月13日立案受理。华某公司起诉请求:1.判令张某停止侵害“中麦578”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2.判令张某向华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3.判令张某赔偿华某公司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15267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某负担。事实和理由:华某公司依法取得了在黄淮冬麦区南片独家生产、加工、经营“中麦578”小麦新品种的权利。2023年8月,华某公司经过调查发现张某未经许可销售“中麦578”授权品种的小麦种子,侵害了华某公司的合法权益。华某公司遂在公证取证后提起本案诉讼。
张某一审辩称:张某只是从事商品粮收购并对外销售,收购的商品粮包含“中麦578”,其对外销售的优质麦的价格和市场上正常的商品粮价格相符,与华某公司所谓的种子价格存在巨大悬殊。张某正常的销售单价仅仅为每斤1.5-1.6元,符合商品粮市场价格,远远低于“中麦578”麦种的价格,作为正常的种子购买者也不会认为以商品粮价格销售的优质麦属于种子。此外,张某既未在收购时对收获物进行提纯性的区别收割,也从未对收购的毛粮进行筛选、发芽率检测、烘干、包装、贴牌销售等行为。张某从来没有欺骗华某公司、将商品粮冒充麦种销售的意思表示,只是华某公司误导张某,利用张某表述的不准确性达到其恶意诉讼的目的。综上所述,张某将毛粮作为收获材料,不是作为繁殖材料销售,销售的目的是食用和加工。张某也未向华某公司保证销售的商品粮具有麦种的稳定性和繁殖性能。至于购买者购买商品粮后的目的是否用于种子粮使用,张某无权过问和干涉;商品粮购买者如果购买后经过筛选、发芽率检测、烘干等加工工序后将商品粮用作种子使用,其种植风险应当由购买者承担。本案华某公司显然也不是正常的购买者,其购买的目的并非是用于种植,而是意图误导张某获取单方证据,通过诉讼获取额外赔偿。综上,张某没有进行生产和繁殖,其只是收购种植户的粮食作为商品粮销售,华某公司要求其停止生产、繁殖、作为种子销售以及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没有事实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华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与本案品种权有关的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第2020014830号植物新品种权证书的记载,种属为小麦、品种名称为“中麦578”的品种权人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某甲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科院某甲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乙研究所(以下简称农科院某乙研究所),培育人为何中某、阎某、张某甲、田宇某。品种权号为CNA20171916.8,申请日为2017年7月21日,授权日为2020年7月27日,保护期限为15年。
2022年11月8日,农科院某甲研究所、农科院某乙研究所向安徽隆某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某公司)、华某公司出具授权书,载明:“中麦578”已经通过河南省品种审定,审定编号:豫审麦20190057。现授权方共同授权隆某公司、华某公司在黄淮冬麦区南片该品种适宜区域开发具有知识产权小麦新品种“中麦578”,两公司具有在授权区域内独家生产、加工、经营该品种的权利。授权期限自2023年10月1日至2032年9月30日。2023年9月11日,农科院某甲研究所、农科院某乙研究所向隆某公司、华某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两公司有权在其品种使用权授权区域内单独以其自身名义对侵害“中麦578”品种权的行为调查取证、申请证据保全、提起民事诉讼、申请诉前或诉讼保全、提起上诉、申请执行、收取法律文书、收取和解款或执行款项等权利。授权期限自2019年9月1日至2032年9月30日止。
(二)与本案侵权行为有关的事实
为证明张某实施了涉案被诉侵权行为,华某公司提交了时间戳认证证书一组及公证购买被诉侵权产品的公证书等证据。
根据华某公司提交的时间戳认证证书,其中TSA-04-20231026794282432证书取证时间为2023年10月26日,取证内容系取证人员对抖音名称“江苏连云港灌南某粮食贸易张某”(以下简称张某抖音号)部分作品内容的录屏。取证的视频作品标题显示“大量求购单一品种新麦……中麦578、伟龙169,镇麦,郑麦系列各种优质麦,普麦,装车秒到账,有货请联系张某”(发布时间2023年8月5日)、“有需要纯的单一的优质品种麦可以联系”(发布时间2023年8月2日,该条视频内容标有中麦578文字)。
证书编号TSA-04-20231116241155687的时间戳认证证书取证时间为2023年11月16日,其内容系取证人员对微信名称为“江苏连云港灌南某粮食贸易张某”(以下简称张某微信)朋友圈发布部分内容的录屏,取证显示该微信朋友圈发布有“大量求购江苏地区雨前单一品种新麦26,新麦45,02-1、伟龙169,中麦578……,质优价高,并求购入库麦联系人张某1385****619欢迎来电”(发布时间2023年7月2日,附视频)、“中麦578种子粮”(发布时间2023年7月31日,附照片)、“单一品种中麦578正在装车”(发布时间2023年8月2日,附视频)等内容。
证书编号TSA-04-20231011577735252的时间戳认证证书取证时间为2023年10月11日,取证内容系对取证人员与张某微信2023年8月至9月期间聊天记录的录屏。记录显示取证人员与张某于8月15日成为微信好友,取证人员当日问:“您好老板!”“多少钱一斤?”张某回应:“1.6。”取证人员问:“筛选好,装上袋多少钱一斤?”张某答:“不筛。”取证人员回应:“不筛我们也不好拉呀。”张某问:“要多少?”取证人员随后语音回应,大意大概为:“六百多亩地,大概需要两三万斤。”“村里还有种地户没买,差不多可以一起买。”“河南小麦都发芽了不能种了。”张某回复称:“河南那边好多都是这边小麦拉过去做种子的。”“还有西农979。”取证人员称:“他们都是代售种子的。”“可我是自己种的,没有设备,还麻烦。”张某回应:“这边过筛也麻烦。”“我来问一下。”随后张某答复:“过筛要多一毛钱一斤。”取证人员问:“筛选好装上袋多少钱一斤吧1.75可以吗?”,张某问“大概需要多少的?”取证人员回应称:“五六千斤左右。”,张某问:“够吗?二百亩少了吧。”取证人员回应称:“不过我们还有几个种地也没有买,我跟他们说说,看他几个要多少。”张某称:“过几天过来看过再说吧。”取证人员问:“装和袋多少钱一斤?”张某答:“就你说的价格。”取证人员回复:“好,过几天我先去看看。”;8月31日,张某微信询问取证人员:“你好!小麦啥时候要?”取证人员未回应。9月2日,双方进行微信通话,时长3分18秒,张某随后向对方发送电话号码138*****619。9月5日,取证人员向张某发送微信消息,内容为:“我侄子大概明天上午去你那儿,我让他顺便带回几袋,如果带回来我们哥几个看了可以,我把定金给你打过去,过几天我就去你那儿拉大概3万8千左右,你给筛选好装好袋就行了老板。”张某随后回复:“好的。”9月8日,张某向对方发送了其银行卡号。9月9日,张某向对方询问:“你好!小麦啥时候要?”对方未及时作出回应。9月22日,取证人员询问:“老板您好,我看种子质量还可以,也差不多,还有吗?如果有给我留一些。”张某问:“要多少?”答复称:“2万多斤。”张某问“可以的,还是要筛好的吧?”答复称:“当然要筛好的啦!”张某随后回复:“要的时候说一声,好筛。”
根据河南省漯河市地汇公证处2023年9月19日出具的(2023)豫漯地证内民字第2170号公证书(以下简称第2170号公证书)的记载,申请人郑州鼎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潘红某于2023年9月6日来到该公证处,称受权利人的委托负责小麦种子维权事宜,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同日,该公证处指派公证员张玉某、公证员助理王某与鼎某公司工作人员冯冰某一同前往取证。当日10点05分,冯冰某拨打备注名称为“灌南某粮食贸易张某”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冯冰某称:“老板我今天来你这买几袋种子,我到你发的位置这了你在哪过来接我一下吧。”随后上述人员到达灌南县新安镇大圈乡一处显示“灌南县大圈粮库”的地方,见到张某及随行人员。公证处工作人员及冯冰某跟随张某来到场地内标示为“5”的库房。冯冰某询问:“这个有没有精选?”,张某回应称:“没有精选,要了再选,也不多了。”冯冰某问:“地上堆放的小麦是什么品种?”,张某称是“中麦578。”冯冰某称:“俺叔他们有个圈子都想要,家里的小麦种子都发芽了。”,张某称“种淮麦也行。”,冯冰某称:“淮麦没有种过,之前种过这个。”张某称:“这个也不多了,就剩这么多了。”冯冰某问:“这个种子产量能产多少啊?”张某答:“正常一千多斤。”,冯冰某称:“买的时候可要精选啊!”,张某称:“到时候会把精选的机器抬到这边。”冯冰某问:“纯度、质量、芽率咋样?”,张某答:“芽率90%以上。”冯冰某称:“现在这个库里面都是中麦578吧,到时候别装错了。”,张某答:“都是一样的。”与张某随行的女子称:“这个库里面的300多万斤都卖完了。”冯冰某随后购买了148斤的“中麦578”,通过扫描张某收款码微信支付235元,付款截图显示备注为“中麦578种子款”。冯冰某问:“这个合多少钱一斤?”张某答:“是1.6元。”冯冰某问:“到时候要的话是什么价位?”张某答:“要的话到时候会精选,不是这个价,是1.9元一斤。”张某又给了一小袋“淮麦33”小麦种子。公证处工作人员对上述取证过程进行了录音录像拍照。购买结束后,公证处工作人员将购买取得的“中麦578”带到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新东南路灌南农机物流农业街*号楼一层曼某酒店附近进行拍照、封存,冯冰某从购买的2袋中取出部分小麦种子进行混掺后,进行拍照、封存,对封存的5个样品进行编号(封存编号20230906-Z-ZM578-01至20230906-Z-ZM578-05)。封存后交由鼎某公司保管。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明上述取证过程均与实际情况相符。公证书附图显示取证购买的产品无正式包装,张某一审庭审中陈述取证产品的包装物为其借来的肥料袋。
华某公司将前述取证封存的“中麦578”(封存编号20230906-Z-ZM578-01)及其提供的“中麦578”种子样品送往河南中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委托该公司对其提供的两份样品做真实性比对。2023年10月31日,该公司出具检验报告,结论为:“根据《NY/T2470-2013小麦品种鉴定技术规程SSR分子标记法》,该样品与对照样品经用42对SSR引物进行DNA谱带数据比对,差异位点数为2,判定为近似品种。”
综合以上取证事实,华某公司主张张某未经权利人许可实施了涉案“中麦578”种子销售行为,且从取证的张某自述内容来看,张某明确陈述可以进行筛选,具备种子生产能力。对于其主张的繁育行为,无相关证据佐证。
(三)与张某抗辩主张有关的事实
张某主张其销售的为“中麦578”小麦品种的商品粮,并非种子,其行为并不构成侵权。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其提交如下证据:
1.2023年9月至10月间,微信“河北孟某小麦价格共享交流群2”聊天记录内容截图。聊天记录内容显示思某原粮部发布的收购通知载明,9月份小麦优质麦收购价格为1.63元/斤、1.65元/斤,“中麦578”为1.67元/斤。10月份通知载明“中麦578”价格1.66元/斤。拟证明2023年优质麦的收购价格在1.7元/斤左右,而种子价格远远高于该价格,张某向华某公司取证人员销售的产品是优质麦,并非“中麦578”种子。
2.山东菏泽华某面粉厂刘玉某与张某的微信聊天截图,表明张某向对方销售“中麦578”“伟龙169”小麦,对方要求其邮寄样品进行化验。
3.河南新乡思某面粉厂郭得某与张某的聊天记录、送货司机陶利某、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该聊天记录中的小麦验质单、结算证明、付款记录等。结合上述证据,证明张某从事粮食贸易,其所收购的粮食用于销售给面粉厂,与河南新乡思某面粉厂10月12日发生的贸易额为228160元,共计2车货。张某对外一直是以商品粮的价格,及每斤1.6-1.7元对外出售,不存在出售繁殖材料的情况。
4.张某合伙人薛某与淮阴区收购点王某的微信聊天及贸易记录截图,表明从2023年8月,张某陆续向王某销售商品粮,贸易金额为211760元、212490元,证实张某从事的是粮食贸易,并以1.6元-1.7元每斤的价格对外出售,不存在出售繁殖材料的情况。
5.灌南县科某家庭农场的投资人陈玉某于2024年11月11日向张某出具的证明一份以及转款记录,证明内容为:“本人2023年6月份,小麦卖给张某,品种为中麦578,重量195吨左右。”用以证明张某的粮食来源来自于种植户陈玉某种植的“中麦578”收获物。
6.灌南县地某家庭农场的前投资人孟令某于2024年11月10日向张某出具的证明一份以及转款记录,证明内容为:“我在2023年6月份卖给张某粮食收购是中麦578,大约150吨左右。”孟令某提供了2022年9月28日,周法某向其出具的农家乐种子农药经营部销售清单,载明种子名称“中麦578”,单价2.5。证明张某的粮食来源于种植户孟令某种植的“中麦578”收获物。
针对张某提交的上述证据,华某公司认为相关证据不能证明张某并未以繁殖材料向外出售。
一审庭审中,张某针对在购买被诉侵权产品前及取证购买时,就双方合意达成时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的含义进行了解释。其主张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是:华某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张某在聊天过程中一直称想购买优质麦作为种子种植试试看,张某只得向对方告知其收购的粮食确实是种植户种植的“中麦578”品种的收获物,是否能够种植由对方自行决定。张某在沟通过程中表示的产量、芽率等实际上指向一般种子“中麦578”的正常指标,而非张某销售的收获物的确定指标。对方作为种植户应当对此完全予以知晓,因此其也仅购买少量回去进行试验是否能够直接种植。故取证内容不能证实张某具有销售种子的意图。
(四)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事实
华某公司一审庭审中陈述,“中麦578”种子的市场零售价格为3.7元。关于该品种对应的商品粮价格,华某公司解释称市面上销售小麦不会单独销售某一品种小麦,而是分为优质麦和普通麦销售,“中麦578”属于优质麦,其价格受市场影响存在波动,最高不超过1.6元。
华某公司主张其为制止本案侵权行为,支出了公证费、取证费、检测费、住宿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并提供了部分费用支出凭证。
一审法院认为:华某公司经品种权人农科院某甲研究所、农科院某乙研究所共同授权,享有生产、加工、经营涉案“中麦578”品种的权利。且经授权,有权单独以自身名义对侵害“中麦578”品种权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故华某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本案中,张某认可涉案被诉侵权产品系其销售,亦对该产品为“中麦578”小麦品种不持异议,但辩称其所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并非繁殖材料,而是商品粮,系收获材料。鉴于涉案品种“中麦578”系常规作物小麦,其本身具有双重属性,既可以是繁殖材料也可作为收获材料,就张某是否实施了销售涉案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综合分析如下:首先,张某系从事粮食收购与销售的市场经营主体,其对于涉案“中麦578”品种小麦本身具备繁殖材料及收获材料的双重属性应为明知。因其不具备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的行政许可,也未获得“中麦578”品种权人的授权许可,其在从事涉案“中麦578”品种商品粮的经营时,理应规范指示产品属性,审核交易对象资质,避免使具有繁殖能力的“中麦578”商品粮成为侵害涉案品种权的源头。但本案中,张某并未履行注意义务,在明知购买者购买“中麦578”小麦作为种子使用,仍对外出售具有繁殖能力的“中麦578”小麦,该行为对品种权人造成了实质损害。其次,张某在对涉案产品的宣传以及被诉侵权产品购买的沟通环节中,相关标的物均能够指向繁殖材料。根据华某公司提交的张某微信朋友圈取证截屏有关“中麦578种子粮”的宣传内容,可以认定张某明确宣称其所销售的产品具备繁殖能力,可以作为种子使用。另根据在案微信聊天记录及公证书记载内容显示,涉案被诉侵权产品的购买人已向其明确表示了其购买产品作为种子使用的意图,张某亦向对方回应“河南那边好多都是这边小麦拉过去做种子的”,表示其所销售的小麦能够作为繁殖材料使用,能够满足对方购种需求。从双方洽谈提及的种植面积、数量需求相关内容,亦能够体现出张某有将本案小麦商品作为繁殖材料向对方出售的意图。此外,取证过程中出现了芽率、产量等指向种子质量指标的问题,张某均向对方予以明确回应,亦反映出其所销售的产品满足种子标准,具备繁殖能力。审理期间,张某虽对其意思表示进行了解释,表明其不具有将涉案被诉侵权产品作为繁殖材料销售的意图,但从双方合意达成的情况来看,张某明知对方有购买涉案被诉侵权产品作为繁殖材料的意图,在其自身不具备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情况下,积极促成涉案被诉侵权产品交易,其主观上具有销售涉案被诉侵权种子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销售涉案被诉侵权种子的行为。综上,结合双方洽谈购买涉案产品时的交谈内容,能够认定张某系将涉案被诉侵权产品作为繁殖材料销售。
关于张某是否实施了生产、繁殖涉案品种繁殖材料行为。鉴于一审庭审中华某公司明确表示,其并未有证据证明张某实施繁殖行为的事实,故其该项诉请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对于生产行为,华某公司主张,取证时张某明确表示可以对被诉侵权产品进行筛选,筛选即为生产行为。但从双方合意内容来看,筛选系依取证人员的要求而为之,并不能当然证明该行为即为种子生产行为。华某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张某经营场所存在种子生产设备,具有种子生产能力,故对其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
张某实际实施了销售涉案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华某公司要求其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本案中,华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张某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亦无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可供参照。综合考量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张某实施侵权行为的性质以及其销售涉案侵权产品的规模、价格、情节以及华某公司为制止本案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定张某赔偿华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5000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七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六条、第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害涉案‘中麦578’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二、被告张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安徽华某种业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合计25000元;三、驳回原告安徽华某种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85元,由原告安徽华某种业有限公司负担3335元,被告张某负担350元。”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华某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某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判令张某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张某并未实施销售授权品种繁殖材料的行为,不构成侵权。(一)张某从事粮食贸易经营活动,对于购买者购买小麦后的具体用途,张某既无权干涉,亦无实际能力管控。张某并非种子销售专业人员,不具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开展常规小麦销售业务时,要求其逐一审核交易对象资质,苛责过高。张某以商品粮价格出售小麦时,对购买者后续若将所购小麦用作种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并不知情。(二)华某公司工作人员采用欺骗手段购买产品,利用张某正常的销售心理,购得价值235元的148斤小麦充作种子,还声称回去后查看能否当作种子使用。一审认定张某应承担赔偿责任显失公平。(三)一审法院在认定“中麦578”兼具繁殖材料与收获材料双重属性的情况下,仅凭臆测认定张某所售产品为繁殖材料,与客观事实相悖。按常理,侵权行为人销售收获物冒充种子旨在谋取非法高额利润,毕竟种子价格通常为收获物价格的2-3倍,但本案中张某的销售价格不能体现出其销售的是种子。(四)双方交谈过程中涉及的标的物描述、指标表述,仅为张某销售产品时针对“中麦578”所作的常规性介绍,不足以认定张某处收获物的具体指标。华某公司当时亦表示需购回后核实化验,这同样表明张某的表述仅属常规业务范畴内的正常说明。同时张某在微信中一直向对方询问“小麦啥时要?”,而非“种子啥时要”。张某微信朋友圈中关于“中麦578种子粮”的取证截屏,其表意并非指收获物可直接当作种子使用,而是强调该收获物源自种植户种植的“中麦578种子”所产出的优质粮食即“优质麦”。华某公司向张某明确表达购买产品用作种子的意图后,张某回应“河南那边好多都是这边小麦拉过去做种子的”,属于常见促销用语,符合商业惯例。因华某公司工作人员冒充种植户,张某在洽谈中提及的种植面积、数量、芽率、产量需求等内容,亦完全契合正常交易沟通习惯。综上,张某出售的收获物系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的繁殖材料种植所得,且出售用途为非繁殖目的的食用、面粉加工等。华某公司工作人员虽称购买目的为种植,但并非是张某诱导华某公司工作人员将其用于繁殖目的。张某并非是向专门从事未经授权的种子繁殖的企业进行销售,并无主观侵权故意,在未造成任何危害后果的前提下,认定张某承担赔偿责任于情于理不符。
华某公司辩称:(一)张某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求购“中麦578”,表明其宣传指向的是繁殖材料,公证书记录了购买全过程,对“中麦578”的相关特性均进行了说明,可以证明其销售的是种子。张某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二)关于被诉侵权种子的销售价格问题,虽然与正规种子销售价格存在差距,但并不能据此否定作为繁殖材料销售的侵权行为性质。在交易中存在多种原因,不能用价格判定产品属性。(三)张某主张华某公司采用欺骗手段购买产品,但在购买过程中华某公司声称购买种子,张某也在积极回应。华某公司不存在欺骗行为。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查,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因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在2021年修正的种子法施行日(2022年3月1日)之后,故本案应适用2021年修正的种子法。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张某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二)如张某构成侵权,赔偿金额应当如何确定。
(一)张某是否存在侵权行为
张某上诉认为,其销售的是商品粮,不知道且无法干涉或管控购买者之后的用途;其不是销售种子的专业人员,无能力审查购买者的资质,其不构成侵权;其不可能冒着侵权风险,以商品粮价格销售种子,否则无利可图。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经审查,第2170号公证书记载,在购买种子过程中,取证人员冯冰某以家里的小麦种子都发芽了为由询问种子、产量、纯度、质量、芽率时,张某积极回应“种淮麦也行”,并对产量、芽率率等作了回答。上述公证事实系客观记录,可以证明张某在销售“中麦578”过程中,明知对方意图购买繁殖材料并以繁殖材料进行销售。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二)》第九条规定,被诉侵权物既可以作为繁殖材料又可以作为收获材料,被诉侵权人主张被诉侵权物系作为收获材料用于消费而非用于生产、繁殖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已有证据显示张某将被诉侵权种子以繁殖材料进行交易的情况下,张某既未举证证明交易者将小麦用作收获材料,又未举证证明其尽到了相应的注意义务。最后,销售价格仅是判断被销售的小麦用作收获材料还是繁殖材料的因素之一。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九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仅凭价格不足否定其销售繁殖材料的事实。故张某有关其销售的并非繁殖材料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张某主张,华某公司采用欺骗手段购买产品,利用了张某的正常销售心理,其并无侵权主观故意。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涉案编号为TSA-04-20231116241155687的时间戳认证证书显示“中麦578种子粮”的内容的发布时间为2023年7月31日;编号为TSA-04-20231011577735252的时间戳认证证书显示张某称:“河南那边好多都是这边小麦拉过去做种子的”;第2170号公证书记载:“与张某随行的女子称:这个库里面的300多万斤都卖完了。”以上证据可证明张某从事种子销售活动,作为经营主体,其理应遵守种子法关于种子销售的相关规定。其次,根据涉案公证书记载,取证人员流露出购买种子的意思,张某积极作出回应,且公证书附图显示取证购买的产品无正式包装,证明张某主观上具有销售种子的主观故意,双方就购买种子达成合意。涉案公证行为是基于张某的侵权行为所形成的证据,张某关于华某公司采用欺骗手段购买产品的主张,缺乏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张某将“中麦578”作为繁殖材料销售正确,张某的行为构成侵权。
(二)关于本案赔偿数额的确定
种子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植物新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本案中,华某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张某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亦无品种权许可使用费可供参照。综合考量涉案植物新品种权的类型、张某实施侵权行为的性质以及其销售涉案侵权产品的规模、价格、情节以及华某公司为制止本案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一审酌定张某赔偿华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25000元,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张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5元,由张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 霞
审 判 员 高俊华
审 判 员 潘才敏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纪宁宁
书 记 员 徐常宏
免责声明: 本站法律法规内容均转载自:政府网、政报、媒体等公开出版物,对本文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请核对正式出版物及咨询线下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