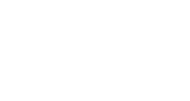宁波某企业、合肥某公司等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其他案由执行监督执行裁定书
案号:
(2024)最高法执监204号
案由:
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其他案由
公开类型:
公开
审理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审理程序:
执行审查
发布日期:
2024-09-05
案件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4)最高法执监204号
申诉人(申请执行人):宁波某合伙企业。
负责人:陈某,该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俊,广东昊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俊锋,广东昊乾律师事务所律师。
利害关系人:长沙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少华,上海市锦天城(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宁洁,上海市锦天城(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合肥某有限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
被执行人:湖南某有限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
申诉人宁波某合伙企业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安徽高院)(2023)皖执复180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宁波某合伙企业向本院申诉,请求:1.撤销安徽高院(2023)皖执复180号执行裁定;2.维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合肥中院)(2023)皖01执异89号执行裁定。主要理由是:一、安徽高院将湖南某有限公司金融业务(含债权债务)分离出来与某某信用合作社(合并改组成长沙市银通城市信用合作社(简称银通信用社)的事实认定为合并分立,即使合肥中院作出的法律认定错误,也不应当影响本案变更、追加长沙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结果。二、安徽高院纠正合肥中院法律认定错误,却继续适用错误的司法解释条文,得出结论必然错误,又在司法解释之外假借诉讼时效、接受财产范围等事由拒绝处理实体问题,违反不得拒绝裁判原则。三、安徽高院认为合并分立的,接受分立财产的企业应当在接受财产价值范围内对分立前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属于法律适用严重错误,安徽高院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明文规定进行审查,严重违反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的法定主义原则。四、本案的基本事实系在改制过程中发生的分立又合并,安徽高院片面采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部分规定的观点进行说理并裁判,失之偏颇,导致严重不公。五、宁波某合伙企业基于湖南某有限公司分立又合并的事实向长沙某公司主张债权,先是通过审判程序追索被驳回,然后才通过执行程序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且执行程序中又经过一次发回重新审查,最终法院却未对实体问题进行处理,造成司法程序空转,如果按照安徽高院的建议再次起诉,则存在明显法律障碍。
长沙某公司提交意见称,宁波某合伙企业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主要理由是:一、湖南某有限公司将其金融业务及相关债权债务划转银通信用社的行为,既不属于企业合并,也不属于企业分立。二、湖南某有限公司将其金融业务及相关债权债务划转银通信用社的行为,可能属于湖南某有限公司转投资的情形,也可能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均需要通过实体诉讼程序予以审查确认。三、湖南某有限公司将其金融业务及相关债权债务划转银通信用社的行为,不符合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定情形,而是需要在实体诉讼程序中审查判断是否发生债务转移的情形。四、宁波某合伙企业在对长沙某公司提起诉讼被错误裁定驳回起诉后,应当通过再审进行救济,而不应错误的选择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程序。这才是导致程序空转、司法资源浪费的根本原因。五、本案在实体方面,长沙某公司也不应承担案涉债务。
本院认为,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申请变更、追加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应对当事人主张变更、追加的事实要件是否成立,应否予以变更、追加进行审查并作出认定。本案中,宁波某合伙企业以本院(1998)经终字第311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中国人民银行某分行以***文件进一步明确批复,1995年底,湖南某有限公司的金融业务和投资业务分立,投资业务由当时还在拟议中的‘某投资公司’承接(未设立);金融业务与某某信用合作社合并组成银通信用社,相关的债权债务划转银通信用社承接”等事实为依据,主张湖南某有限公司先分立后合并形成银通信用社,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应变更、追加银通信用社目前的承继主体即长沙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长沙某公司则主张湖南某有限公司将其金融业务及相关债权债务划转银通信用社的行为,既不属于企业合并,也不属于企业分立,而属于转投资或其他情形,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法院应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并根据证据规则,对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的湖南某有限公司与银通信用社是否构成合并或分立的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并在事实认定基础上对应否变更、追加长沙某公司为被执行人作出裁定。但安徽高院认为长沙某公司是否承担以及在多大范围内承担案涉债务应通过审判程序认定,未对湖南某有限公司与银通信用社是否构成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合并或分立进行审查和认定,而是直接撤销了合肥中院(2023)皖01执异89号执行裁定,程序不当,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此外,因为宁波某合伙企业已另案起诉长沙某公司要求其承担案涉债务,但已被相关法院以应在执行程序中解决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所以,在执行程序中审查也更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综上所述,宁波某合伙企业的申诉理由部分成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1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皖执复180号执行裁定;
二、指令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宁波某合伙企业的复议申请进行审查。
审 判 长 王富博
审 判 员 熊劲松
审 判 员 尹晓春
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孙 超
书 记 员 增 斌
1
免责声明: 本站法律法规内容均转载自:政府网、政报、媒体等公开出版物,对本文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请核对正式出版物及咨询线下律师。